这是一块圣地,近百年来这里成长着中国数代最优秀的学者。丰博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人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出的精神魅力。科学与民主已成为这块圣地不朽的灵魂。
——谢冕在一九九七年迎新会上的讲话

教授 老北大的魅力
在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浸透于它的每一个方面。在教员队伍的构成上,更显现其精神之所在。几十年间,北大以它宽阔的胸襟和气魄,吸引了众多不同学科、不同见解的学者和大师们,而他们所表现出的智慧的魅力、学术的魅力、性格的魅力、人格的魅力,无不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北大的学子,他们的轶闻趣事被一代又一代北大人传颂。
“兼容并包”精神下的教授们
1916年蔡元培先生出任北大校长,在启用教师上更体现其“兼容并包”之精神和“学术自由”之主张,他提出:“广延积学与热心的教员,认真的教授”,以“提起学生研究学问之兴会”。他用才的宗旨是:见解主张可不相同,学术论点可不相同,但学问不可以不高深,品行不可以不严谨。他赴任后,随时延揽人才,聘用了许多新教授。这当中有革新派、提倡白话文,主张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有复辟派、主张恢复帝制,拥护袁世凯做皇帝的急先锋辜鸿铭、刘师培等……;有最早把共产主义介绍给中国的李大钊、也有最早介绍无政府主义的李曾石、还有最早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夏元瑮……;此外他还启用了钱玄同、俞同奎、沈尹默等一批老北大的老人,更启用了只有二十三、四岁的梁漱溟等一批年轻人……,还请来了刚从欧洲回来的女教授陈衡哲先生、聘用了数学系老教授冯祖荀,外籍教授、地质系的葛利普等。同时裁去了一批陈腐守旧、道德败坏的人物。

辜鸿铭

鲁迅

冯祖荀

汤用彤

罗家伦

林语堂

傅斯年
这一切在用人上的改革措施,无不体现了蔡元培先生旧学旧人不废,而新人新学大兴的主导思想,使教授队伍素质得以大大提高,给学校带来了研求学问的好学风,也为日后北大教授之列的整体特色奠定了基础。
自蔡元培先生起,北大往者可继,来者可追。组成了一支人才济济的北大教授队伍。文科学长陈独秀、理科学长夏元瑮、法科学长王建祖、工科学长温宗禹。以后撤学长制而设系,又有总务长蒋梦麟、教务长顾孟余、英文系主任胡适之、化学系主任俞同奎、物理系主任顔任光、哲学系主任汤用彤等,还聘用了法文系教授杨芳、德文教授朱家骅、法律系教授何基鸿、经济系教授马寅初以及林语堂、傅斯年、冯友兰、罗家伦等一批优秀教授。
“学术自由”下的教授们
北大的研求学问之风盛行于教授其间,他们治学严谨,颇下功夫,而北大又有其兼容并包之特色,故同门类不同派别的学问之争在此十分普遍。他们坚持已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已见。他们常常以捍卫真理的态度来抵挡别人的评价,而对对方的问题,往往亦是针锋相对,毫不留情。这种争论充分表现了学术民主,给予了学生充分开阔眼界之空间,培养了学生们独立思考和探索真理的兴趣和能力,同时教授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研求学问的精神也对学生产生了较好的影响。
如,五四时期,古文家刘师培先生与今文家崔适先生对门而居,互为邻里,每日朝夕相见,总是相敬如宾,互称先生,并伴以一鞠躬。而在学术上二位则观点相左,一到课堂上,情景大变,彼此攻击起对方的谬误来言辞严厉。
又如,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在老子的年代及《老子》一书的时代问题上意见不同。按胡的说法,老子是春秋晚期人,略早于孔子;而按钱的说法,老子是战国时人,略早于韩非子。因胡的观点先已在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言及,于是争论之始,胡适按兵不动之态,钱穆则起笔挑战,而胡依然不认可,于是便引来了一日胡钱当面的对峙:一次教授会上二位先生相遇,钱先生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了。胡先生说:钱先生,你举的证据并不能使我心服;如能使我心服,我连我老子也不要了。两人大笑不已。钱穆是经胡适提携进北大的,可见其不计个人恩怨的科学的学术批语精神,而胡适也很宽容,当一同学问及钱先生讲得与他不同,究竟谁的对时,他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们应该自己去选择,看哪个是真理。”
据曾为北大学生的王昆仓先生的回忆文章所载:

哲学对台戏的两位主角:梁漱溟

哲学对台戏的两位主角:胡适
还有一个哲学唱对台戏的故事。一是胡适先生所讲《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个是梁漱溟先生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个是留学美国的洋博士讲中国哲学,一个是布衣布褂的土学者讲东西文化,并且在同时同地的两间教室中。这场哲学对台戏吸引了许多的学生,因为两位都学术高深、学问精道,不仅讲得头头是道,而且各有所长。
这种研求学问之风也深深地影响着学生们,他们善于思考,敢于提出问题和自己的观点。这种精神亦得到了教授们的赞赏和鼓励。
一次名教授钱玄同先生讲授文字音韵学中的关于广东音韵,课下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给钱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对其所讲提出不同意见。下次上课,钱先生面带微笑站在讲台上,问:“哪位是李锡予同学?”李站了起来:“我就是。”钱先生客气地说:“请坐!你的信我已看过了,你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不是广东人,对广东的音韵只是一知半解,很感谢你纠正了我的纰漏。”接着他读了李锡予的信,还希望大家今后发现讲课中的纰漏,要提出自己的意见。
还有一次,胡适先生讲课,提到某小说时说:“可惜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位同学站起来反驳说,有人说过,并指出在什么丛书的什么书里就有。胡适先生很惊喜,以后上课常常提及此事,并逢人便讲“北大真不愧为大”。
正是北大此种自由探讨之学风,使老北大在学术研究上收获颇丰:
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应用资产阶级观点方法写成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1920年,李大钊《唯物史观》课程,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列入大学教程。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开山之作。 钱玄同等提出《新工标点符号修正案》在全国颁布执行。
1921年,邓之诚著《中华二千年史》在史学界影响很大。
1923年,商承祚著《殷墟文字类编》为最早的甲骨文字典。
1924年,孙云铸撰《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为中国第一部古生物专著。
1925年,刘半农发表《四声实验录》。
1926年,李四光著《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创建地质力学理论。 顾颉刚等编《古史辨》,创“古史辨派”。
1930年,朱光潜著《文艺心理学》,在美学界形成重要流派。
1932年,熊十力著《新唯识论》。 曾昭抡参与发起“中国化学会”。 钱穆著《先秦史》成一家之言。
1933年,孟森主持明清史料整理。
1934年,从吾讲授匈奴史及辽金元史,成为奠基人之一。
1936年,丁绪贤著《化学史通考》第一部化学史专著。
1940年,金岳霖著《论道》,
1943年,邓广铭著《宋史职官志考证》
1946年,冯友兰著《贞观六书》。
教授们课堂上的魅力

学生们非常喜欢钱穆先生讲课,课堂上从来就是座无虚席
“丰富的学识,闪光的才智,庄严无畏的独立思想,这一切又与耿介不阿的人格操守以及勇锐的抗争精神相结合,构成了一种特殊的精神魅力。”这充分地表述了北大教授们的无限魅力之所在。
在北大,没有严格的课本,没有讲课深浅之规定,也没有课时进度之约束,一切都由教师们根据情况而定。在这样的课堂上,教授们的智慧在此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教授们的学风在此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教授们的个性在此得到了充分地张扬。
如果我们以课堂为载体,聚集起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以讲课为引线,串连起大师们多姿的风范,便更能够从中体味到其魅力之所在。
蔡元培先生在北大讲授的惟一课程是《美学》。一位同学的回忆录中记载下当时课堂的情境:“他教的是美学,声浪不很高,可是很清晰,讲到外国美术的时候,还带图画给我们看,所以我们觉得很有趣味,把第一院的第二教室完全挤满了。第一院只有第二教室大,可坐一二百人,……挤的连讲台上都站满了人,于是没有办法,搬到第二院的大讲堂。”
胡适先生的演讲式教学在学生中很受欢迎,亦常常因红楼教室人满为患而搬入二院大讲堂。他讲课从不发讲义,自己也没有讲稿。讲课内容也有些特点,如讲中国文学史(宋元明清部分)时,先从文学评论的角度,介绍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讲《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时,给学生们介绍了曹寅写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但学生们最喜欢的还是他的演讲。柳存仁先生在其《记北京大学的教授》文中写到:
胡先生在大庭广众间讲演之好,不在其讲演纲要的清楚,而在他能够尽量地发挥演说家的神态、姿势,和能够以安徽绩溪化的国语尽量地抑扬顿挫。并因为他是具有纯正的学者气息的一个人,他说话对的语气总是十分的热挚真恳,带有一股自然的气所以特别能够感动人。
钱穆先生亦是学生们喜爱的教授。他所担任的课程,中国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中国通史等,从来都是两个小时连起来讲,中间不休息,他讲课的地点从来都在二院大讲堂,而且从来都是座无虚席。朱海涛先生《北大与北大人》中写到:
一付金属细边眼镜,和那自然而然的和蔼,使人想到“温文”两个字,再配以那件常穿的灰布长衫,这风度无限雍容潇洒。向例他总带着几本有关的书;走到讲桌旁,将书打开,身子半倚半伏在桌上,俯着头,对那满堂的学生一眼也不看,自顾自的用一只手翻书。翻,翻,翻,足翻到一分钟以上,这时全堂的学生都坐定了,聚精会神的等着他,他不翻书了,抬起头来滔滔不绝地开始讲下去,越讲越有趣味,听的人越听越有趣味。对于一个问题每每反复申论,引经据典,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这种充实而光辉的讲授自然而然地长期吸引了人。

鲁迅先生的课堂上,时时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
鲁迅先生讲课虽不像演说家的演讲,但课堂上却时时沸腾着青春的热情和蓬勃的朝气。听课的不仅是国文系的学生,还许多其他系及校外的青年学生,甚至还有从外地赶来专门听他的课的。同学们反映听他的课就像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说法很不同。”
此外,还有刘师培先生,他作为北大中国文学的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学生们认为水平确实很高,他上课既不带书,也没有一张卡片,而是讲台上一站,随便谈起,头头是道,所引古文资料,常常是随口背诵,同学们都很佩服。他的文章也做得漂亮,可谓“下笔千言”。
教授中还有一类是口才较差,学问很高深的。如周作人先生,大概是将满腹学问都注入笔端了,而讲起课来却很不善言辞,一口很不好懂的浙江口音,走上讲台后常常有点手足无措,许久才站定,然后把两手分别插入棉袍的兜儿里才慢慢讲下去,吞吞吐吐,且说且噎。

顾颉刚先生常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
梁漱溟先生大概也应算在此列之中。他讲印度哲学概论、大成唯实论、东西文化及哲学等课,有甚多的见解,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但却不善于言辞,可惜的是文字也欠流畅,每当讲到某个道理时常不能即兴说明,便急得用手触壁或是用手敲头深思。
顾颉刚先生,乃“疑古学”之大家,著有《古史辩》。先生学问渊博,擅写文章,但口才偏差,讲课时常常词不达意,吃吃一会,情急之下,索性拿起粉笔在黑板上疾书,写得速度很快也很清楚。

孟森先生讲课时从来不向台下看
还有明清史专家孟森先生,其学问亦是很高深的,但却属不擅讲课之例。学生们回忆:他永远穿着一件旧棉布长衫,面部沉闷,毫无表情。他的讲课也是出奇的沉闷。有讲义,学生人手一编。每次上课必是拇指插在讲义中间,走上讲台。他讲课从来不向讲台下看,照本宣读,下课时,讲义合上,拇指依然插于讲义中间,转身走去,依然不向讲台下看。
不善讲者的教授中也有因自家口音实在难懂,讲,不如不讲者。如陈介石先生,他在哲学门(系)也是深受同学们的尊重的,他讲中国哲学史、诸子哲学,还在历史门(系)讲中国通史。他讲课也是以笔代口,先把讲稿发给大家,上课时一言不发,就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课铃一响,粉笔一扔就走了。最难得的是他虽不讲话,但却是诚心诚意地备课,课堂所写与于讲稿亦各成一套。据说就是因其一口难懂的温州土话的缘故,却促成了他的一种风格。
朱希祖先生亦在此列。他的海盐话有的北方同学听到毕业,也没听懂几句,真不如粉笔写更好了。为此还常常闹出一些笑话。一次朱先生讲文学史,讲到周朝,反复说孔子是“厌世思想”,同学们都很奇怪,黑板所引孔子的话都是积极的,怎么是厌世呢?过了许久,同学们才解开此谜,原来朱先生所谈为“现世”而非“厌世”。
讲课中有的教授以阐述自己的观点为主,也有的教授则更注意前人的错误。陈恒教授便是这样。在讲课时他将二十五史从头讲起,把所有有关的事件一一交待清楚,特别是尤其注意前人的错误。有的同学回忆陈先生时说:
“在他眼里,前人的错误不知怎么那么多,就像他是一架显微镜,没有一点纤尘逃得过他的眼睛。不,他竟是一架特制的显微镜,专挑错误的。……他的嘴相当利害,对于错误的学者批评得一点也不留情。”
教授中也有讲课喜欢标新立异者,有时异到胡说、离奇之地步。林损先生便是代表之一。据说他长于记诵,许多古籍都能背诵,诗写得也很好。但上课经常发牢骚、讲题外话,有时随口胡说。他讲杜甫《赠卫八处士》时,竟说:“卫八处不够朋友,用黄米饭炒韭菜招待杜甫,杜公当然不满意,所以诗中说‘明日隔山岳,世世两茫茫’,意思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后来他在学校整顿中被解聘。

刘半农
还有北大著名怪人辜鸿铭先生,他虽然其常年身着枣红马褂,拖着一条长辫,坚持复旧,保皇复辟,但其在学问上亦是佼佼者,据说他所著的《中国人的真精神》曾被誉为是“一部震炫欧洲思想界的煌然巨著”。他精通英、德等多国语言,主讲西洋文学,后又主讲英诗。既便是后来蔡元培先生解聘了他,也不是因其学问不精,而是因其教书不认真。他上课常带一个童仆为他装烟倒茶,他坐靠椅上,慢吞吞地讲课,一会儿吸水烟,一会儿喝茶,学生们着急地等着他。后来竟一学期只教了学生六首英诗。
黄侃先生与辜鸿铭、刘师培曾为老北大三怪杰,其讲课的奇闻更是让人哭笑不得。田炯锦先生《北大六年琐记》中回忆:
“有一天下午,我们正在上课时,听得隔壁教室门窗的响动,人声鼎沸。下课时看见该教室窗上许多玻璃破碎,寂静无人。旋闻该班一熟识同学说:‘黄先生讲课时,作比喻说:好像房子要塌了。方毕,拿起书包,向外奔跑,同学们莫明究竟,遂跟着向外跑。拥挤的不能出门,乃向各窗口冲去,致将许多玻璃挤碎。’”
教授们的轶事与趣闻点滴
钱玄同、刘半农出演的“双簧戏”。故事发生在五四时期,主角是钱玄同先生和刘半农先生。在新文化运动中二位教授都是运动的主要倡导者,1918年,钱先生等人在《新青年》上对封建文化发动攻势的时候,除了少数顽固派的反对外,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为了打破这沉寂的空气,二位先生便合演了一场有名的“双簧戏”。于是在《新青年》上出现了一位化名叫王敬轩的顽固派所写的洋洋数千言的反对新文化运动、攻击《新青年》的文章《文学革命之反响》,此后刘半农便针锋相对地写了万余言的反击文章《复王敬轩书》,把顽固派的思想主张批驳得体无完肤。这样一来,果真扩大了新文化的影响,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展开。而这位王敬轩其实并无其人,而是由钱玄同先生所扮。
刘文典触怒蒋介石被拘。刘先生为国学大家。每日口不离烟,常口衔一支,虽在与人讲话烟却依然粘在唇边。先生性情幽默滑稽,善谈笑,只是语不择言,常常触怒对方。一次见到蒋个石,直呼其名,使蒋大为不满,找人传话斥责他,刘仍不改口,蒋遂下令逮捕,而刘仍毫不在乎,后经蔡元培等名流出面说情,才恢复了自由。
陈独秀激出个书法家。沈尹默先生诗好,更擅长书法,老北大时北大的一院、二院、三院门前所挂的长牌上所书均出自其手。说起沈先生的书法却与陈独秀有着一段故事。一次,未曾谋面的陈先生来到沈先生家拜访,一进门便大声说:“我叫陈独秀,昨天我看到了你写的诗,诗做得很好,字其俗入骨。”话虽刺耳,但却激发了沈先生,从此沈先生发奋研究起书法来。
顾颉刚戏里悟出的《古史辨》。顾先生是个戏迷,但他看戏既不注重演员的扮相,亦不注重演员的唱腔,而更感兴趣的是戏中的故事。同是一个故事,许多剧种中都有,但细节却各不相同。看多了,顾先生发现一个规律:戏出的越晚,故事情节越细,所加枝节越多,由此推到古史上,经手的人越多,编造的东西便越多。这便是顾先生《古史辨》基本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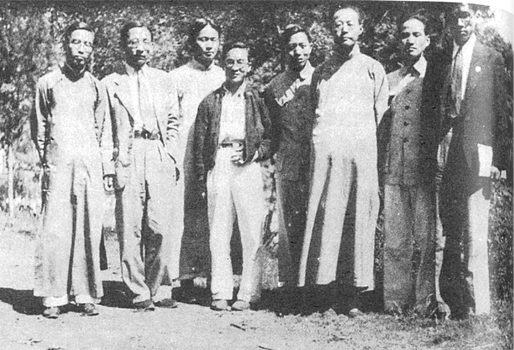
顾颉刚与国史研究会
三沈三马轶事。提起北大名人总少不了要说的是三沈三马,一来因为一家兄弟二三人竟都与北大关联,本就是不易,更何况这几位先生又都是老北大之才人,名气很大。
三沈本籍南方吴兴人,却均在陕西长大,于是身上便少了些江南的纤柔,多了些北方人的直爽。沈大先生名为沈士远,先在北大教国文,后转入燕大。沈二先生沈尹默名气最大,诗人、书法家,一位难得的艺术家。沈三先生名沈兼士,曾任老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
三马,一是马幼渔先生,家中九兄弟中排行为二,马二先生很早就进了北大,教国文。马二先生为人谦和,宽宏大量,据说他的其他几位兄弟常年轮流被他接到北京家中读书,说是进行熏淘,结果其他兄弟果真有了出息。还有一位马先生是家中排行为四的马衡先生,任北大史学教授,还曾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来四先生去了故宫博物院,当了院长。第三位马先生是马家排行为九的马廉先生,曾在北大教文字音韵,1935年竟病故在讲台上,其后北大以重金收购了九先生的珍贵藏书。
卯字号里五先生。 当年文学院还在马神庙四公主府时,文科楼西面的几间平房曾作为文科教员的预备室,一人一间,许多名人常在这里聚集,巧的是这中曾有过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这或许是“卯字号”之称的由来吧。 两只老兔子是朱希祖和陈独秀, 三只小兔子是胡适、刘半农、刘文典。这五位先生都为当年老北大名人,而“卯字号”也成了北大人传说的佳话。
白雄远的柔与刚。 白先生为学校所聘的军事训练课教员,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挂有少将军衔。 他身材魁梧,双目有神,身着军服,扎皮带,蹬皮靴,一身戎装,十分威武。 然军事训练课虽为学生必修课,但常常不被学生们所重视, 白先生虽在课上煞有介事,一丝不苟,但课下总是平易亲近学生,大家都很喜欢他,特别是考试时,他常是高抬贵手。一次,期未考试,他将试题出于黑板上,便有学生要他解释题意,他便根据答案要求原原本本地解释起来,学生们边听边答卷, 还不时地说: 先生,慢些说。 就这样大家高高兴兴地交了卷。
白先生对学生宽容,对下属教官们则十分严格。当时他还任北平市学生军军训总监。一次在红楼后大操场全市学生军大检阅,有一个学校的学生没打绑腿,带队的教官也没打, 白教官问他为什么,教官答学生们都没打,白先生严厉地斥责到:“你是学生吗?你是军人,军人出操怎么能不打绑腿呢?”这时的白教官和平日真是判若两人。
辜鸿铭的怪。说到北大第一怪人辜鸿铭,周作人先生有这样一段描述:
“北大顶古怪的人物,恐怕众口一词的要推辜鸿铭了吧。他是福建闽南人,大概先代是华侨吧,他的母亲是西洋人,他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头上一撮黄头发,却编了一条小辫子,冬天穿枣红宁绸的长袖方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说在民国十年前后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时代,马路上遇见这样一位小城市里华装教士似的人物,大家也不免要张大了眼睛看得出神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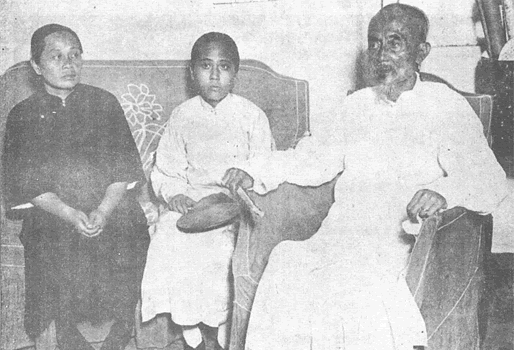
辜鸿铭一家
辜鸿铭的怪不仅在装饰上,主要在思维上,他从小受西洋教育,还国语都不会说。却因在一次偶然遇到一位留法的中国博士,才知道了《易经》、《论语》、《春秋》等经典和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便开始学汉语,读古书,由心到行,由内到外,迅速成了带有某种偏执和执迷的的厚中薄洋、复古保皇派。辜鸿铭的举止亦十分怪异。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回忆在一次与辜的会面中,被辜鸿铭极尽讽刺挖苦之能势嘲弄了一通后,临走时送给了他两首辜自己写的诗,后来毛姆请人译出一看,原来是两首赠妓女的诗,弄得毛姆哭笑不得。袁世凯称帝不成,终忧郁而死,北洋军阀下令全国衰悼,辜却成心作对,请了戏班,一闹了三天,出了保皇不成之怨气。辜鸿铭行事怪,说话也有两怪:一是骂人,他性格孤僻,愤世嫉俗,看不惯之事敢骂、善骂。二是诡辩,说话幽默,又胡搅蛮缠。他主张男人纳妾,竟说什么男人好比茶壶,女人好比茶杯,一把茶壶配上几只茶杯,不是很自然的事情吗。
数不完的教授,说不完的名师,讲不完的故事。这就是北大,这就是北大的教授们,在北大这块沃土上,留下了他们研求学问、追求真理的足迹。只可惜我们不可能一一列下他们的名子,不能一一留下他们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