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毕业20年,变化的是同学们的样貌,不变的是对纯真美好的大学年代的记忆与怀念。韩晓征校友和大家分享她大学时代的故事,通过“军训”、“图书馆”、“看禁书”、“死亡”、“理解”五个片段,带我们回到属于他们的80年代。
我读僧肇的《物不迁论》时候,最欣赏如下的华彩之句:“江河兢注而不流,野马飘鼓而不动”,觉得这些动静一如的景象,有时就可以理解为记忆。
这次的毕业二十年聚会,临近午夜,老同学之间如此难舍难分,大概也是因为我们共同拥有一段色彩纷呈的记忆。
这里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自己二十年不灭的几组记忆蒙太奇,是我生命的组成部分,随着岁月流逝,历久而弥新。

1989年10月,北大中文系87级部分女生于天坛公园合影
前排(从右至左)
谢凌岚,叶英姿,刘颂,刘曼雪
后排(从右至左)
肖永凤,胡兰江,张谦,刘宁,程敏,韩晓征,周静
蒙太奇之一:军营·萝卜地·“守纪”
大一的第一堂重课无论如何当推军训。
第一件为我始料不及的事情,就是同学们各自背着行李集合,排着队走上车站的天桥去等火车。那一刻我背着巨大的由被子褥子衣衫杂物组成的如山的包袱,在一种逆来顺受的心情背景之下,在火车站清冷的路灯照耀之下,想着人生的不可得兼——临出门之前,慈母满怀柔情一针一线、絮了又絮、惟恐不厚的褥子和被子,此刻悉数变成了肩上沉重的负担。
不过肩上的负担,证明着肩膀的存在,肩膀的存在,证明着“我”的存在,而冰冷苍白的路灯,伸向不明远方的铁轨,都让我在一瞬间,对于自己为何背了那么大个包袱,身边的人为何都背了各自的包袱站在那个铸铁牢笼般的天桥之上,等着一列或许永远不会开来的火车,产生了种种的疑问和错觉。
一群城里的只知道死读书的学生娃,到了军营之中,到了连排班长的绳规之下,每日里顶着毒日头正步走来走去,几天就是一次野营拉练,倒也无甚余话可说:有个身体,只管按口令做去就是。
只不过,身体需要吃饭,尤其每天的活动量巨大,而饭食又有那么一点点寡淡,于是乎,每日里顾不上疑问和错觉,只想着生存与排泄。
小时候容易面子薄,偶遇人、事的不合,很可能拂袖而去。然而在军营中,太阳下面操练了一整天,饥肠辘辘站在饭堂门口,被喝令着再三高唱军歌,声音不高不许吃饭时候,心里虽有阵阵抵触,却是不曾拂袖而去的——那个稍稍在心之下的胃袋,以利嘴一般由内啃噬的顽强,牢牢控制了形而上的心和形而下的腿。
可是不知为何,无论怎样放下了淑女的架子风卷残云,过不多久,又是饥肠辘辘(回京才知是得了甲亢)。于是跟着饱读书卷却又同样饥肠辘辘的谢凌岚,一道往军营的操场那边疾行。

谢凌岚校友
凌岚当年的广博已令我叹服——整个晚上,她可以从普鲁斯特的病态、张爱玲的荒凉、余英时的绵里藏针,一直聊到量子力学和松果体的神秘——然而那个黄昏的饥饿时分,几乎没有任何神秘可言,我们只是相跟着默默疾行。
军营的操场,几乎就像所有军营操场的格局一样,东西两侧是篮球架,正北是礼堂,三面合围的,是廉价而单调的泡桐树——那些枝叶硕大无朋的速成树种,是华北军营不生动趣味的生动写照。
我在树下徘徊之际,凌岚已风风火火从对面的男生宿舍跑了回来,把手中袋子哗啦抖开,里面是一位先生赠送的香肠和巧克力等等高热量禁时候的美味,我们席地而坐,狼吞虎咽之后,方才渐渐感到心绪的复归平静,于是乎不知不觉,慢慢开始谈论席慕容、舒婷等人的诗句,或者恋爱与失恋的话题。
可是当凌岚吟咏那名句“天空证明我的纯洁……”时候,两人正好经过操场西北侧的萝卜地,我又感到阵阵饥饿小嘴的撕扯,于是从萝卜地里拿起一只萝卜,到旁边的水管处略做冲洗,就与凌岚分而食之——凌岚挥刀切削萝卜的样子,有若狂士割腥啖膻一般豪迈。食毕,见对面墙上赫然刷着标语:“遵规守纪”,不免相顾大笑,遂篡改方才诗句云:“天空证明我的纯洁,萝卜地证明我的守纪。”
蒙太奇之二:图书馆·旧报纸·雕像的背影

大概是1988年吧,正逢北大建校九十周年纪念活动,应校刊之约,写了一篇散文,题为《我是你水边一只丑小鸭》,被收入《精神的魅力》一书,里面的种种感受随着岁月流逝,几乎都已淡忘,唯有如下一段,至今记忆犹新:
在天井里读书。从四楼阅览室的窗子朝下望,看见领袖像高大的身形和长长的影子……那天在社科期刊阅览室浏览,抬眼看见灰色铁架子上,一摞厚厚的《人民日报》合订本,黑色的封皮,有1955年的,1958年的,1966年的,1976年的……心里很激动。我的目光应该投向更深远的地方,我应该不断为自己打开新的窗口。
然而,此书出版不久,正当我这无知学子希望把目光“投向更深远的地方”时候,才发现一扇刚刚打开的“新的窗口”被砰然关闭了——当我像往常一样,再去四楼期刊阅览室想要查阅旧报纸合订本,却被告知根据新的规定,旧的报纸期刊杂志不再向本科生开放了。那一刻我这一向迟钝的头脑,于瞬间开始学习并建立着因果联系:是偶然,还是必然呢?难道两者之间,真的有些关联么?
再从阅览室的窗口下望,雕像的后背沉默如高墙,直到从他脚下走过,这才发现,依然有“长长的影子”,笼罩着我等这些微末如蚁的生命。
蒙太奇之三:禁书·限时·布帘
古文献专业的刘宁,甫一入学我们就一见如故。
军训时候,也曾并肩坐在军营墙头,全不管近旁即是猪圈,泰然相互应和着,曼声背诵“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幼年时候因为父亲深爱古文,也曾受到一点点熏习,上大学之前还曾因此稍有自负。可是入学见到刘宁,方知自己是井底之蛙——井外不仅是群山连绵,更是山外通海的。
文献专业的功课大多艰深似海,若遇浅显美文,刘宁常不忘与我分享,读罢则相视而笑,悠然会心。
文献科目之一的版本学,我对其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不过对于八九十年代多种名著再版过程中的所谓“洁本”,却是一直心怀腹诽——前人心血之作,您老凭什么抡起板斧删削?您所删削的,是精华?是糟粕?岂能由您一言定夺?况且何为“洁”?何为“不洁”?您老既是生来即为“洁”,焉知何为“不洁”?……总之,种种不平意绪常于胸中起伏冲突,亦曾将腹诽道与刘宁等知己。
却说忽有一日,刘宁突然一脸严肃地急急唤我去她们宿舍,进了门刻不容缓,将厚厚一册重重抵到我怀里:“快看快看!朋友好不容易借来的,分给我两小时,匀你一小时,后面一帮人排队等着呢,快啊!”说完,复又坐回到书桌边,专心研究她的儒家经典去了。
我低头一看,却原来是全本的《金瓶梅》,脑子里就是轰然一响,赶忙坐到最近的一张下铺,刚要打开,想了想,又鬼使神差地拉上了布帘……
一小时后,我打开布帘,神思恍惚地将那全本捧还给刘宁,她看看手表,更无多言,夹着书一阵风冲出门去,送达那些翘首盼望的下家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不知是谁的床上,“乜呆呆,闷悠悠”地,回味着。
家里有一套《金瓶梅》,洁本,大致是翻过的,这一回邂逅全本,阅读又严格限定在一个小时之内,那种感觉,怎么说呢?
有如俗人被迫进到庙里,不得已吃了整年的素,一旦还归俗世,恰逢满汉全席,那可真是,只拣肥腻膏腴招呼——还必须瞄着日影儿悉数吞下——有点,因为霎时之间快速的进食,感到微微地,恶心。不过恶心之后,则是一种鲜有的轻松。
走出那间背阴宿舍,心里更是渐渐铺展开一派明朗透亮——哈,俺终于“不洁”了一回!掀起禁忌帘幕之一角,窥见了神秘经典的“全貌”,这种感觉——这一个小时的平等与自由,真好,亲身体会了,什么是“兼容并包”。
蒙太奇之四:绒花·竹席·死亡
三十六楼南侧的甬路两旁,当年有几株合欢树,每逢夏季,总要缀满如云的绒花,远看如透明晚霞,近看,则不再觉出那红云的娇美——大概因为体质的缘故吧,自己一闻到绒花那种甜得发腻的味道,胃里就开始莫名搅动。

那年夏天,眼看考试临近,我记得很清楚,是下午最后两节古汉语课,讲课的老师温柔敦厚,酷暑中同学们有的犯困,有的聊天,老师也不在意,还是温声地传道授业。这时候忽然有个声音从教室后头传来:“太吵了,我得坐前面去。”循声而望,只见邹文凯同学拿着书本,已经坐到了第一排,继续专心写着笔记。
他就在我的左侧一米之遥,脸上红红的青春痘粒粒清晰。
下了课,从食堂吃罢晚饭出来,经过合欢树林,努力穿过那道甜腻浓香的屏障,我平抑住胃里的涌动,再次困惑于那花香中隐隐的邪恶因何而来。
于黄昏的微光中爬楼,刚爬到一半,迎面来了同宿舍董豫,她平日美丽热情的脸庞,这时候笼着一层阴云,匆匆走过我身边时候,只说了两个短句,有如电影中的谶语:“你妈妈来了。邹文凯死了。”
懵然走到宿舍门口,看见我那笃实得可爱的母亲,抱了一床高高大大卷成一捆的竹席等在那里,一边心里叹着“其情可感”,一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那床双人的旧竹席折了又折安顿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竹劈儿折断时刻,总会发出轻微的“咔咔”喧响。
一边跪在竹席上铺床,一边听着母亲和史月光、董豫她们有问有答,得知就在课后这两三个小时之内——邹文凯和几个同学骑车到校外游泳,出了事。人已停进了校医院太平间。
竹席硌得膝盖处的皮肤现出浅浅的纹路,想起一出河南曲剧名叫《卷席筒》:老年间的贫民,身后不过是一领竹席一裹,随即入土而已。
晚上跟母亲道别,又随同学们去了校医院附近徘徊片时,终于星散,各回宿舍安歇。
回来再经树下,遍地绒花落英,这才悟道,那种甜腻得有似腐烂的邪恶气息,似乎正是象征了死亡。继而想起他脸上那红红的青春痘——青春与死亡原是两极,却在这绒花的红泥中融作一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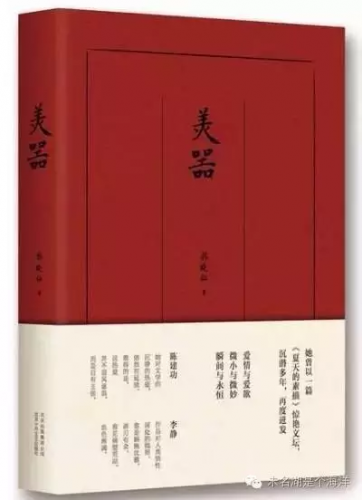
蒙太奇之五:“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这次的二十年聚会,不停地跟老同学们干杯,以至于午夜时分,我跟凌岚都是半醉,相携着打车回家。
于微醺的朦胧中遥望窗外,满眼都是跳动的明灭灯火,灯火如彗星,随着汽车的飞驰,拖下长长亮亮的彗尾;再想到聚会上的摇曳光影,不觉又忆起老杜的名句:“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这次同学会之前不久,刘宁来电聊天,说起她们中学时候的语文老师八十大寿那天,再次给前来祝寿的学生们上了一堂语文课,讲的就是杜甫的《赠卫八处士》。让我不禁想起去年刚刚过世的父亲——这也是父亲最喜欢的杜诗之一: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
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
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
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
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
怡然敬父执,问我来何方。
问答乃未已,儿女罗酒浆。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
主称会面难,一举累十觞。
十觞亦不醉,感子故意长。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二十多年前,在新源里的旧家,那小小房间昏黄的灯光里,父亲逐字逐句为我讲述着,字面意思我仿佛都能理解,可也只是字面的理解。待父亲讲到“惊呼热中肠”时候,顿了一顿,轻轻说:“孩子,这种感受,你不到一定岁数,是很难理解的。”二十多年后,十一岁的儿子热闹,为了从我这里争取到周末玩上一小时电脑游戏的“指标”,不得不耐着性子,跟妈妈诵读《赠卫八处士》,念到“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时候,每回都要恶作剧地“哦儿”上一声,说是“模仿‘惊呼’呢”……
我非但没有制止那怪叫,反倒感觉那叫声中的童真俏皮,让人心生阵阵微酸。于是顿了一顿,抚摸着小小少年稚嫩的肩膀,轻轻说,“孩子,这种感受,你不到一定岁数,是很难理解的。”……
2011年6月3日
北京

韩晓征(摄影:谢凌岚)
韩晓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说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硕士。著有《夏天的素描》《美器》《耶稣传》(合著)等书。作品曾获“十月文学奖”、上海电视台“中学生最喜爱的作品·知音奖”、北京大学中文系与台湾新地文学基金会联合颁发之“郭枫文学奖”等奖项。